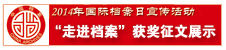记忆中,我对档案的最初认识,缘于父亲的一次平反:教育界是当年“文革”的“重灾区”,父亲就是在那场浩劫中被错划成“右派”。那年,我刚刚出生,襁褓中的我随父母下放到农村。身份的落差让能说会道的父亲整天沉默少语,就连我也无故成了“黑五类”后代,没有玩伴,人家象避瘟疫一样,远远地躲着我……
这种沉默生活直到我十三岁那年,党中央“拨乱反正”对十年“文革”浩劫造成的冤、假、错案进行集中清查处理。父亲仿佛看到了希望,他不停地向上级教育部门申诉,但遗憾的是:教育局怎么也找不到父亲当年的档案,包括对他处理的只言片语。时隔数十年,父亲的档案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就是没了踪迹。父亲还是照样不停地申诉,包括寻找当年参予此案的当事人,三次去西安,五次上衡阳,旅途的劳累自不必说,单申诉的材料摞起来就有好几尺高。这样来来回回三年问题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,父亲气得差点把申诉材料烧了,可心里又觉得憋屈,整天眉头紧蹙,能说会道的父亲从此变得沉默寡言,劣质的烟草成了父亲唯一的消遣方式。
就在父亲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,他从前教育界的的一个老同事,风风火火地跑到我的家里,还在门外就嚷到:老袁,老袁,有希望了……父亲听到这没有头绪的话,也不知是喜是忧,自嘲地说:“这么多年,没希望咯?”“真的,你的档案找到了,有希望了”这时的父亲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笑容,但心里还是犯嘀咕:为了找档案,市教育局档案室就差翻了个底朝天了,为什么在不抱希望的时候它自己就出来了呢?怎么找到的?这时老同事告诉父亲:“你的档案资料不在教育局,是在邻近一家科研单位找到的,是他们在清理档案时,发现有教育局的档案,就退回来了。”这时的父亲才真真切切地相信眼前的事实,有了这份迟来的档案,父亲很快就平反了。至于,父亲的档案是如何流失的,又是如何流落到八杆子打不着的科研单位,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同样与档案有关的事也发生在我的身上,不过没有父亲那么悲怆,我只有惊喜和自豪。原企业改制,我比同期入厂的职工整整多了三年的工龄,为这事有人还告到上级主管部门,只有我心里最清楚:打开尘封的档案,三年偏远山区的支教历历在目……
那年,我正好高中毕业成了“待业青年”。父亲希望我能复读,报考师范类专业好接他的班。我婉拒了父亲的安排,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支教工作,通过考核和短期的培训,我被委派到酃县(现在的炎陵县)的一个偏远山区支教。虽然,我在心里有所准备,但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差。学校就建在一个相对平缓的小山包上,教学条件很简陋,虽然大山里树木多,可学生用的课椅大多破烂不堪,师生的饮用水则要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很远的山坳下去挑。更让我害怕的是到了晚上,大山里没有通电,用于照明的是一盏山里人用的马灯,光线很暗。晚上掌灯也怕,仿佛窗外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你,山风伴着树枝的响声让人瘆得慌。不掌灯更怕,树影倒映在窗台上,随着山风不停地变幻着影子,课椅和门窗被山风吹得吱吱作响,大山里很静,这些细微的声响听得真真的,而且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,遇到雷雨天的晚上,那更是怕得要命……
好在老校长是本地人,个头不是很高,有着山里人的憨厚和质朴,对我们城里来的伢子更是照顾有加。师生的饮用水都是他天还没亮就挑满了,我们日常用品都是老校长从山下带回来。在他的带领下,我们在学校的附近的山凹里开垦了一块菜地,解决了师生的吃菜问题。老校长的话不是很多,他用行动默默地关心和爱护着我们。每到晚上,老校长总爱到校区内转转,只要有一点点响声,老校长会习惯性的干咳两声,到后来我们也习惯了,只要没有听到老校长的咳嗽声,我们倒睡不踏实。
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在惶恐和老校长的关心下很快过去了,最让感动的是来年开学的时候,老校长早早地等在长途汽车站,同来的还有几个高年级学生,他们都是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帮我来拿行李。老校长显得特兴奋,不断地嘘寒问暖,当时,我都感动得差点落泪……后来听老校长说,全公社三个支教青年只有我回来了,也只有我坚持完成了三年的支教工作。教育局领导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,按当时的政策,三年的支教工作可计算工龄,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早把这档事忘了,不想在企业改制的时候,我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。
父亲因档案沉冤得以昭雪,我则因档案获得了实惠。更重要的是,我在三年的支教工作中,养成了吃苦耐劳、严谨的工作态度。这在我后来从事档案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,我深知档案不论对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一个真实的回顾,我们每天都在用行动和智慧书写着自己的档案。接手档案工作以后,我努力做到边学边干,边干边提高。我不仅熟练掌握了档案管理的业务技能,还自学了档案管理计算机应用程序等相关知识。每天面对着这些不会说话的案卷,一个再单调不过,再平凡不过的岗位上,我克服了浮躁不安的情绪,有的只是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。
我爱档案管理工作,更崇尚档案工作的严谨。 |